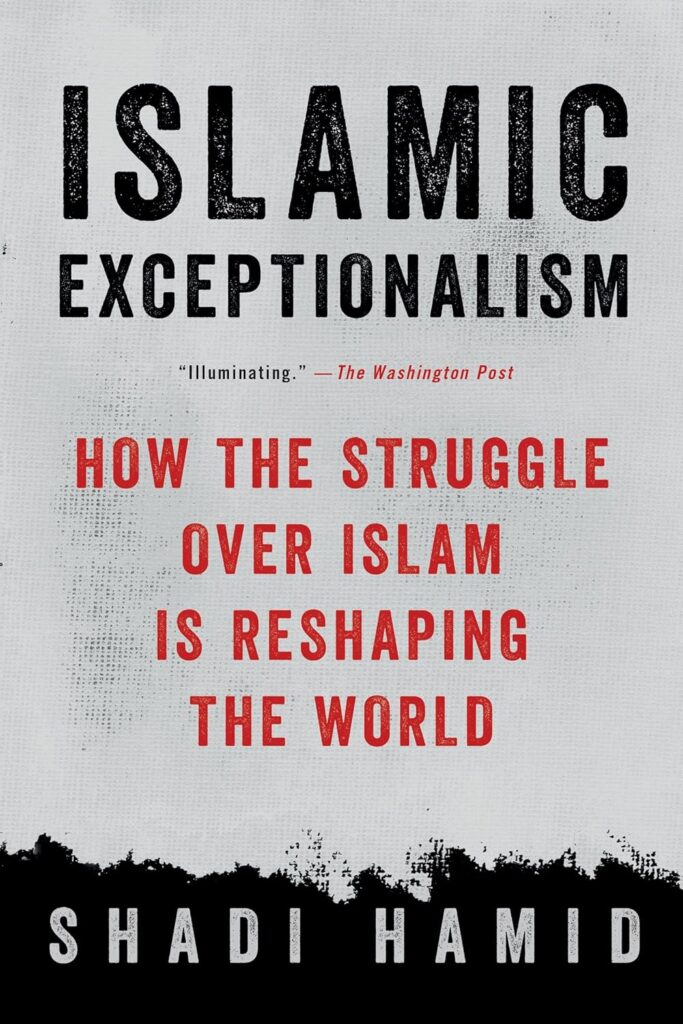
Islamic Exceptionalism: How the Struggle Over Islam Is Reshaping the World, Shadi Hamid, 2017
宗教保守才是深层的地心引力,世俗化反倒像是一种极不稳定的非常态。
当我们观察伊斯兰世界近几十年的政治变迁时,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:土耳其强力推行近百年西化改革后,一旦民主机制运转,选票却一次次把宗教保守派的埃尔多安推上权力巅峰;埃及“阿拉伯之春”后,一人一票选出的不是世俗派,而是主张“伊斯兰是唯一解决方案”的穆斯林兄弟会;巴勒斯坦在西方的推动下举行民主选举,结果民众选择了哈马斯。
这不禁让人发问: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如此艰难?
《伊斯兰例外论》一书给出了一个犀利答案: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就是例外的。这种“例外”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好坏,而是指其“出厂设置”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有着本质区别。
两大宗教的基因差异:从创始人说起
要理解这种差异,我们需要回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时刻。
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在历史学家眼中,其社会身份非常明确:他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持不同政见者。耶稣手中没有政治权力,没有军队,没有领土,大部分时间都在躲避罗马当局的追捕。
那句著名的“上帝的归上帝,凯撒的归凯撒”,在本书作者哈米德看来,其实是早期基督徒为了生存而做出的政治妥协。潜台词是:“皇帝陛下,我不想要您的皇位,我只管灵魂得救的事。”
基督教在创立之初的几百年里,根本没有机会思考如何治理国家、制定法律或征税,被迫发展出了一套在异教徒统治下生存的神学——承认世俗权力的合法性,同时保持精神独立。政教分离某种程度上就是基督教的原始状态。
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则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他在麦加传教时确实也是受迫害的少数派领袖,但迁徙到麦地那后,一切改变了——他成为了国家建设者。
在伊斯兰教的创世纪中,没有凯撒站在先知对面,因为先知本人就是凯撒。他不仅是神的使者,还是最高行政长官、最高法官和最高军事统帅。
这意味着在伊斯兰教的出厂设置里,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是完全重合的。《古兰经》和《圣训》中记载的不仅仅是道德劝诫,还有具体的法律条文:如何分配遗产、如何惩罚盗窃、如何发动战争。
圣书的本质区别
两教圣书的性质也大相径庭。
对基督徒来说,《圣经》是上帝的话语通过人类作者记录下来的,带有人的风格和时代印记,这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。
而在伊斯兰教义中,《古兰经》是真主直接的逐字逐句的言语,不是穆罕默德编写或转述的。它是神谕本身,被认为是永恒、超越时空的,一个字都不能改。
当神在经书中明确规定了遗产继承比例和对某些罪行的惩罚,这就不是建议,而是神的律法。这种对文本神圣性的极致强调,使得伊斯兰教法在现代冲击面前表现出了惊人韧性。
“成功的诅咒”与心理落差
早期的伊斯兰教取得了惊人的成功:在先知去世后短短100年里,穆斯林大军横扫了从西班牙到印度的广阔疆域。这种辉煌的世俗胜利,就是真主眷顾的直接证据,“信仰等于胜利”的等式被深深刻入伊斯兰文明的集体潜意识。
相比之下,早期基督教更像一部苦情剧,连始祖耶稣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
然而,伊斯兰教早期的巨大成功,给现代穆斯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心理黑洞:如果我们所信奉的是真理,如果真主许诺了胜利,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输得这么惨?
从横跨欧亚的辉煌帝国到如今被西方碾压的破碎局面,这种巨大反差在穆斯林心中产生了剧烈的认知失调。主流解释不是“现代文明更厉害,我们应该学习”,而是“我们输是因为不够虔诚,是因为偏离了先知建立的完美政教合一模型”。
这种逻辑非常直接:回到过去,回到那个宗教与政治完美融合的出厂设置。这就是为什么“伊斯兰是解决方案”在众多穆斯林国家有强大号召力——它不是在推销政策,而是在召唤一种失落的荣光。
宗教改革的悖论
西方人常期待伊斯兰世界能出现一场类似欧洲的宗教改革,出现一位“伊斯兰版的马丁·路德”。但哈米德在书中泼了一盆冷水:在伊斯兰世界,宗教改革不是解药,反而是剧毒。
马丁·路德改革的核心口号是“唯独圣经”,要回到早期教会那个贫穷、没有权利、受迫害的状态。而新约圣经的出厂设置恰恰是“我们不要管世俗东西,只要管精神救赎”,因此路德的回归释放了把信仰个人化的力量。
但如果伊斯兰改革者高喊“回到经典”,回到的不是宽容多元的现代世界,而是一个更纯粹、更强硬、更具战斗性的7世纪阿拉伯。因为伊斯兰教的出厂设置是:在战斗中所向披靡的先知、建国领袖、事无巨细的法律条文。
传统的伊斯兰法体系虽显古板,但有一套复杂的制衡机制,宗教学者阶层起到缓冲作用。一旦绕过这个缓冲层,让普通信徒直接面对那些关于战争、刑法和异教徒的激烈经文,结果不是信仰个人化,而是原教旨主义。
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者往往比传统派更加激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ISIS和基地组织就是伊斯兰教的“新教徒”——他们都厌恶传统宗教权威,主张每个人直接阅读和执行经文。只不过,路德从经典中读出的是“因信称义”,而他们读出的是斩首和建立哈里发国。
温和路线的失败与民主自由悖论
那么,走温和路线的“政治伊斯兰”是否可行?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案例给出了残酷答案。
穆兄会穿西装打领带,搞慈善、办医院、做社区服务,承诺通过民主选举上台,以温和渐进方式把伊斯兰价值观注入现代国家。这听起来很完美,但现实却异常残酷。
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,穆兄会在埃及民主选举中获胜,但仅一年后,埃及社会就陷入彻底撕裂。数百万世俗派民众上街抗议,要求军方推翻这个民选政府。最终军队出手镇压,发生了开罗拉巴广场大屠杀。
最令人震惊的是埃及自由派精英的反应:这些满口人权法治的精英,看到穆兄会成员被屠杀时,没有同情反而欢呼。为什么?因为在伊斯兰例外论的引力场里,可能根本不存在温和中间路线。
对埃及世俗派来说,穆兄会上台不是政策分歧,而是生存威胁。一旦他们掌权,就会通过教育、法律重新定义生活方式:禁酒、要求带头巾、把神学渗透进学校。民主选举变成了一场身份战争:要么变成彻底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,要么变成世俗国家。
这就是哈米德指出的残酷悖论:在中东,民主和自由往往不可兼得。如果你想要自由(男女平等、宗教宽容、个人权利),往往得靠独裁者用刺刀压制保守的社会底色;如果你想要民主,尊重大多数人意愿,选出来的极可能就是要求实施宗教法的政教合一派。
结语:接受非自由的民主?
哈米德拒绝提供廉价的安慰,而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二选一:选择不自由的民主(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统治),还是选择不民主的自由(独裁政府的世俗统治)?西方必须学会接受一种“非自由的民主”。只要一个国家愿意搞选举,建立权力和平交接机制,即使选上的政府要求禁酒、戴头巾甚至实行部分伊斯兰法,也应承认其合法性。
这听起来像是现代文明底线的后退,但哈米德认为,对于现在的中东,民主必须先于自由。这是一个悲剧性选择,但可能是唯一现实的道路。
世界大同或许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。伊斯兰世界可能永远不会变成另一个欧洲或美国,它会在神权与人权的剧烈拉扯中,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。我们只能怀着敬畏与警惕,看着这个古老文明在现代惊涛骇浪中,寻找属于它的生存形态——哪怕这个形态并不符合我们的偏好。
伊斯兰例外论的本质不是文明优劣论,而是文明差异论。理解这种深层次的基因差异,或许才是真正对话的开始。